“创客城市”上虞走进“科创名城”武汉
“创客城市”上虞走进“科创名城”武汉
“创客城市”上虞走进“科创名城”武汉潮新闻客户端(kèhùduān) 张广星
 春末一个温和的(de)日子,我又一次走上了(le)通向白石关的古驿道。这是一片(yīpiàn)寂静的、辽阔的山湾,西边耸立着台州市区永宁(yǒngníng)山脉的最高(gāo)峰——590多米的九峰山(jiǔfēngshān)顶,还有九峰山顶下各个侧面看移步换形的丫髻岩。在天清气朗的日子,我们远(yuǎn)在东海椒江口的高楼上向西远眺,能很清晰地看到蹈虚凌空而立的丫髻岩巨石群。山脉从(cóng)这里拔地而起,蜿蜒南去,这一段称之为方山,到了方山这里再折而向东,高低错落,这条山脉是黄岩和路桥之间的分界线,它穿过路桥,向东一直往椒江境内伸展。
春末一个温和的(de)日子,我又一次走上了(le)通向白石关的古驿道。这是一片(yīpiàn)寂静的、辽阔的山湾,西边耸立着台州市区永宁(yǒngníng)山脉的最高(gāo)峰——590多米的九峰山(jiǔfēngshān)顶,还有九峰山顶下各个侧面看移步换形的丫髻岩。在天清气朗的日子,我们远(yuǎn)在东海椒江口的高楼上向西远眺,能很清晰地看到蹈虚凌空而立的丫髻岩巨石群。山脉从(cóng)这里拔地而起,蜿蜒南去,这一段称之为方山,到了方山这里再折而向东,高低错落,这条山脉是黄岩和路桥之间的分界线,它穿过路桥,向东一直往椒江境内伸展。
 在(zài)永宁山脉(shānmài)北向,就是(shì)一望无际的永宁江~椒江冲积平原。这(zhè)里成陆的历史相对比较短,但沿山脉的曲曲折折,则形成了大山湾又套小山湾的湾群组合。而在九峰山~方山(fāngshān)~大仁山之间,组成了永宁山脉的第一个大湾。这个(zhègè)大湾里散落着的几个村庄,全都以“岙(ào)”为名(wèimíng),依次是白龙岙村、东岙村、林公岙村和唐家岙村……从这一个个(yígègè)以“岙”为名的村庄,就可想见这里(zhèlǐ)的地形地貌,那辽阔的绵延的山坡地。这些山坡地土壤肥沃,阳光充足,日照时间长,是水果生长的好地方。别的村庄,农民有山地不是用来种番薯就是种土豆。这两种作物可以抗饿,但江口靠山的村民几乎没有种土豆或番薯的。这里是黄岩的也是中国的名果之乡。
在(zài)永宁山脉(shānmài)北向,就是(shì)一望无际的永宁江~椒江冲积平原。这(zhè)里成陆的历史相对比较短,但沿山脉的曲曲折折,则形成了大山湾又套小山湾的湾群组合。而在九峰山~方山(fāngshān)~大仁山之间,组成了永宁山脉的第一个大湾。这个(zhègè)大湾里散落着的几个村庄,全都以“岙(ào)”为名(wèimíng),依次是白龙岙村、东岙村、林公岙村和唐家岙村……从这一个个(yígègè)以“岙”为名的村庄,就可想见这里(zhèlǐ)的地形地貌,那辽阔的绵延的山坡地。这些山坡地土壤肥沃,阳光充足,日照时间长,是水果生长的好地方。别的村庄,农民有山地不是用来种番薯就是种土豆。这两种作物可以抗饿,但江口靠山的村民几乎没有种土豆或番薯的。这里是黄岩的也是中国的名果之乡。
 现在正是枇杷(pípá)(pípá)的(de)(de)(de)盛果期。当然成熟的枇杷果是金黄色(jīnhuángsè)的,现在果子还(hái)在发育中,果皮是青色的,与叶子的颜色差不多,表皮还有一层白色的细绒。但这(zhè)是我对枇杷青果时候的旧印象,现在枇杷生长成熟的过程,我们都已经看不到了(le),因为枇杷果子都被套上了纸袋子,这就是近十年来逐步推广的枇杷套袋技术。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劲给满树的枇杷套袋呢?一是为避免受物理损伤,如大风(dàfēng)吹刮,容易让枇杷果的表皮擦伤,疤痕累累,卖相(màixiàng)不好。二是防止鸟啄。过去,枇杷果的大多产量都被鸟儿吃了。套袋是一项很繁重的工作,但果农们很用心,很耐心,不管枝高枝低一一套(yītào)袋,这说明了这些枇杷果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之(zhī)重要,期待之殷切。这就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一片(yīpiàn)白色的星星点点,由脚下伸展至极目远处。就好像深绿色的果林上铺上了一层霜雪。而在我们还没进山的时候,远远地看去一层白,又以为是“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的橘花,但又觉得这个季节已经过了橘花的花期。
山湾里静悄悄的,连一丝微风都(dōu)没有。除了我们这些(zhèxiē)偶尔闯入的探访者,看不到一个活动的人影。我想起了十多年前的那一次来访,正是枇杷花盛开(shèngkāi)的隆冬时节,我当时曾写过一片短文《枇杷花是英雄(yīngxióng)花》。人们赞美梅花,但很多雅人只知道凌寒怒放的梅花,却很少有人关注或知道在同样的严寒里,盛开的还(hái)有枇杷花。枇杷花盛开时,山谷里还呈现出一种(yīzhǒng)热烈的气氛,这种热烈的气氛是由(yóu)枇杷花和蜜蜂共同营造出来的。以下是我十二年前的一篇微文:
现在正是枇杷(pípá)(pípá)的(de)(de)(de)盛果期。当然成熟的枇杷果是金黄色(jīnhuángsè)的,现在果子还(hái)在发育中,果皮是青色的,与叶子的颜色差不多,表皮还有一层白色的细绒。但这(zhè)是我对枇杷青果时候的旧印象,现在枇杷生长成熟的过程,我们都已经看不到了(le),因为枇杷果子都被套上了纸袋子,这就是近十年来逐步推广的枇杷套袋技术。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劲给满树的枇杷套袋呢?一是为避免受物理损伤,如大风(dàfēng)吹刮,容易让枇杷果的表皮擦伤,疤痕累累,卖相(màixiàng)不好。二是防止鸟啄。过去,枇杷果的大多产量都被鸟儿吃了。套袋是一项很繁重的工作,但果农们很用心,很耐心,不管枝高枝低一一套(yītào)袋,这说明了这些枇杷果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之(zhī)重要,期待之殷切。这就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一片(yīpiàn)白色的星星点点,由脚下伸展至极目远处。就好像深绿色的果林上铺上了一层霜雪。而在我们还没进山的时候,远远地看去一层白,又以为是“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的橘花,但又觉得这个季节已经过了橘花的花期。
山湾里静悄悄的,连一丝微风都(dōu)没有。除了我们这些(zhèxiē)偶尔闯入的探访者,看不到一个活动的人影。我想起了十多年前的那一次来访,正是枇杷花盛开(shèngkāi)的隆冬时节,我当时曾写过一片短文《枇杷花是英雄(yīngxióng)花》。人们赞美梅花,但很多雅人只知道凌寒怒放的梅花,却很少有人关注或知道在同样的严寒里,盛开的还(hái)有枇杷花。枇杷花盛开时,山谷里还呈现出一种(yīzhǒng)热烈的气氛,这种热烈的气氛是由(yóu)枇杷花和蜜蜂共同营造出来的。以下是我十二年前的一篇微文:
 《且听蜂鸣——记一场山野(shānyě)狂欢》
太阳升上南山已经很高了,唐家岙村后的山湾里还是空无一人,由于这里的山坡地上只种着(zhe)枇杷、柑橘等果树,没有遮天蔽日的浓荫巨木,蓝天显得特别高远(gāoyuǎn)。奇怪的是(qíguàideshì)连一只鸟儿也没有,山谷里虽然明亮(míngliàng)但寂然无声。
初涉此景,几乎令人惊疑恍如梦境。但是,当你一步步走进被枇杷树夹道的(de)古径,你的耳边慢慢地会响起一种嗡嗡嗡的声音,开始时是细微的,单而轻,你并不在意(bùzàiyì),若有若无,若断若续,但这些声音在你的耳边越聚越多,越聚越响,你还没有(méiyǒu)意识到它们是从哪里穿过来的,你眼前还是只有阳光,只有静穆的树,这些声响好像就(jiù)是从地底里,从草丛间,从树的枝叶里传出来的,它们组成了一个越来越(yuèláiyuè)宏大的多声部的合奏,这个时候(shíhòu),你才会觉得(juéde),这是蜂鸣。你才会张大眼睛去(qù)寻找蜂的身影。果然,当你这样想(xiǎng)的时候,蜂就真的在你眼前乱舞。
此时枇杷花正盛开着。虽然世人(shìrén)不识枇杷花,但蜜蜂懂得(dǒngde)。这是蜜蜂冬日里最忙碌也是最欢快的日子。它们不停地飞,从这丛花飞到那(nà)一丛花。那响彻天地的蜂鸣就是在它们飞舞的时候发出来的。
我曾在(zài)一位作家的(de)散文中读到他描写蚊鸣的声音(shēngyīn),说"聚蚊(jùwén)如雷",我以为太夸张了。蚊虫小小的身体怎么能发出如雷的声音呢?今天我在枇杷花盛开的山坡地上可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当千万只蜜蜂在一起共鸣的时候,它们就有了如雷贯耳般的力量。
原来寂静的山野,竟是一片欢乐谷。在这似乎被人类遗忘的地方,蜜蜂和(hé)花(huā)正在展开一场酣畅淋漓、震天动地的忘情交媾。
《且听蜂鸣——记一场山野(shānyě)狂欢》
太阳升上南山已经很高了,唐家岙村后的山湾里还是空无一人,由于这里的山坡地上只种着(zhe)枇杷、柑橘等果树,没有遮天蔽日的浓荫巨木,蓝天显得特别高远(gāoyuǎn)。奇怪的是(qíguàideshì)连一只鸟儿也没有,山谷里虽然明亮(míngliàng)但寂然无声。
初涉此景,几乎令人惊疑恍如梦境。但是,当你一步步走进被枇杷树夹道的(de)古径,你的耳边慢慢地会响起一种嗡嗡嗡的声音,开始时是细微的,单而轻,你并不在意(bùzàiyì),若有若无,若断若续,但这些声音在你的耳边越聚越多,越聚越响,你还没有(méiyǒu)意识到它们是从哪里穿过来的,你眼前还是只有阳光,只有静穆的树,这些声响好像就(jiù)是从地底里,从草丛间,从树的枝叶里传出来的,它们组成了一个越来越(yuèláiyuè)宏大的多声部的合奏,这个时候(shíhòu),你才会觉得(juéde),这是蜂鸣。你才会张大眼睛去(qù)寻找蜂的身影。果然,当你这样想(xiǎng)的时候,蜂就真的在你眼前乱舞。
此时枇杷花正盛开着。虽然世人(shìrén)不识枇杷花,但蜜蜂懂得(dǒngde)。这是蜜蜂冬日里最忙碌也是最欢快的日子。它们不停地飞,从这丛花飞到那(nà)一丛花。那响彻天地的蜂鸣就是在它们飞舞的时候发出来的。
我曾在(zài)一位作家的(de)散文中读到他描写蚊鸣的声音(shēngyīn),说"聚蚊(jùwén)如雷",我以为太夸张了。蚊虫小小的身体怎么能发出如雷的声音呢?今天我在枇杷花盛开的山坡地上可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当千万只蜜蜂在一起共鸣的时候,它们就有了如雷贯耳般的力量。
原来寂静的山野,竟是一片欢乐谷。在这似乎被人类遗忘的地方,蜜蜂和(hé)花(huā)正在展开一场酣畅淋漓、震天动地的忘情交媾。
 再来说说枇杷(pípá)。黄岩曾被誉为“中国枇杷之乡”,黄岩枇杷最高年产量曾占全国的(de)60%。这不是我瞎说的,在(zài)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全国枇杷产销会议在黄岩召开,上述的信息就是(jiùshì)我在这次会议上得知的。当然,那时黄岩还没有(yǒu)被拆分,现在包括永宁(yǒngníng)山南麓桐屿镇在内的整个路桥区都还属于黄岩县,而桐屿镇也是枇杷主产区(chǎnqū)(zhǔchǎnqū)。也就是说,永宁山南北的山坡地,既是黄岩的也是中国的枇杷主产区。现在长江以南枇杷宜产的地区都引种了枇杷作为当地农民的致富产业,这样,永宁山南北两边的枇杷产量在全国的产区中的比例自然有很多(hěnduō)下降,但它们至今一直是,或者说更加是当地农民的摇钱树。如前文已经写(xiě)到的,他们如此用心地给每一个枇杷青果套袋,就是有力的证据。
再来说说枇杷(pípá)。黄岩曾被誉为“中国枇杷之乡”,黄岩枇杷最高年产量曾占全国的(de)60%。这不是我瞎说的,在(zài)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全国枇杷产销会议在黄岩召开,上述的信息就是(jiùshì)我在这次会议上得知的。当然,那时黄岩还没有(yǒu)被拆分,现在包括永宁(yǒngníng)山南麓桐屿镇在内的整个路桥区都还属于黄岩县,而桐屿镇也是枇杷主产区(chǎnqū)(zhǔchǎnqū)。也就是说,永宁山南北的山坡地,既是黄岩的也是中国的枇杷主产区。现在长江以南枇杷宜产的地区都引种了枇杷作为当地农民的致富产业,这样,永宁山南北两边的枇杷产量在全国的产区中的比例自然有很多(hěnduō)下降,但它们至今一直是,或者说更加是当地农民的摇钱树。如前文已经写(xiě)到的,他们如此用心地给每一个枇杷青果套袋,就是有力的证据。
 但永宁山脉北麓的(de)(de)(de)山湾,还是(háishì)另一种近些年来迅速风靡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东魁杨梅(yángméi)的原产地。东魁杨梅的品种名字不是黄岩人自封的,而是中国果树界的泰斗吴耕民教授确定的。所谓东魁,一是指它源于黄岩江口街道(原称江口镇)的东岙村;二是指东方之果型最大者也。每次测体积时,测量者都愿意在东魁杨梅的果子旁放一个乒乓,果然这果子跟乒乓球都一样大甚至更大。这是黄岩东岙村的杨梅农在祖祖辈辈种植杨梅过程中的创造,被(bèi)浙江农业大学的果树教授们发现,通过基因(jīyīn)检测等科技手段进行确认,然后通过扦插等方式进行推广(tuīguǎng)。
东魁杨梅(yángméi)一经面世,就迅速惊艳了(le)世界。惊艳之后,全国杨梅宜产区(chǎnqū)迅速行动起来,引种东魁杨梅,以至于江口的杨梅产业,杨梅果(guǒ)自然是核心,但迅速后来居上的产业是苗木。卖苗木成为了当地农民的新致富门路。有一个靠引种东魁杨梅而成为全县支柱产业、东魁杨梅成为这个县最闪亮的金名片的县,叫仙居县(xiānjūxiàn)。
仙居县与黄岩同在台州区域之内,与黄岩西部相邻,是(shì)典型的(de)山区县,有着适宜杨梅栽培的广阔(guǎngkuò)山地。仙居人把这种世上独一无二(dúyīwúèr)的大果型东魁杨梅看得很重,精心管理,并以县名名之曰“仙梅”。他们的创意策划非常成功,是经典案例,“仙梅”迅即红遍全中国,甚至漂洋过海,飞跃千山万水(qiānshānwànshuǐ),誉及全世界。所以现在的仙梅早已成了世界性的品牌(pǐnpái),当杨梅成熟时,真是一梅难求,价格逐年(zhúnián)走高。也带动了其它地方东魁杨梅的销售价格。
但永宁山脉北麓的(de)(de)(de)山湾,还是(háishì)另一种近些年来迅速风靡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东魁杨梅(yángméi)的原产地。东魁杨梅的品种名字不是黄岩人自封的,而是中国果树界的泰斗吴耕民教授确定的。所谓东魁,一是指它源于黄岩江口街道(原称江口镇)的东岙村;二是指东方之果型最大者也。每次测体积时,测量者都愿意在东魁杨梅的果子旁放一个乒乓,果然这果子跟乒乓球都一样大甚至更大。这是黄岩东岙村的杨梅农在祖祖辈辈种植杨梅过程中的创造,被(bèi)浙江农业大学的果树教授们发现,通过基因(jīyīn)检测等科技手段进行确认,然后通过扦插等方式进行推广(tuīguǎng)。
东魁杨梅(yángméi)一经面世,就迅速惊艳了(le)世界。惊艳之后,全国杨梅宜产区(chǎnqū)迅速行动起来,引种东魁杨梅,以至于江口的杨梅产业,杨梅果(guǒ)自然是核心,但迅速后来居上的产业是苗木。卖苗木成为了当地农民的新致富门路。有一个靠引种东魁杨梅而成为全县支柱产业、东魁杨梅成为这个县最闪亮的金名片的县,叫仙居县(xiānjūxiàn)。
仙居县与黄岩同在台州区域之内,与黄岩西部相邻,是(shì)典型的(de)山区县,有着适宜杨梅栽培的广阔(guǎngkuò)山地。仙居人把这种世上独一无二(dúyīwúèr)的大果型东魁杨梅看得很重,精心管理,并以县名名之曰“仙梅”。他们的创意策划非常成功,是经典案例,“仙梅”迅即红遍全中国,甚至漂洋过海,飞跃千山万水(qiānshānwànshuǐ),誉及全世界。所以现在的仙梅早已成了世界性的品牌(pǐnpái),当杨梅成熟时,真是一梅难求,价格逐年(zhúnián)走高。也带动了其它地方东魁杨梅的销售价格。
 但(dàn)杨梅好吃(hǎochī)果难采。我有一位同事家在(zài)唐家岙村,家里有几十株东魁(dōngkuí)杨梅树。有一年同事邀请(yāoqǐng)我们去他家采杨梅。一般来说,杨梅成熟采收(cǎishōu)时节,也总是(zǒngshì)春雨霪霪之时。江南地区把每年这个时节的连阴雨称之为“梅雨季”,大概就是指杨梅成熟之时恰遇雨势连绵吧。农民总是冒着或大或小的雨登枝或坐一张很高的剪果子用的高凳采收杨梅。但杨梅树的树形总是很高大,农民不得不站起来,尽力伸长自己(zìjǐ)的臂膀,并把镰刀绑在一根(yīgēn)长竹棍子上,尽量伸向更高更远的地方,这样,人的重心容易倾斜。所以我从医院得到的消息说:每年的杨梅采收时节,医院里接收的从枝头或高凳上跌落受伤的伤员总是比平时(píngshí)多出太多了。
东岙村的(de)这棵树(zhèkēshù)龄已超过一百年的东魁杨梅母本(mǔběn)树现在还生命力旺盛,树形高大,独木成林,结果累累。当地人对这棵历经沧桑的母本树有一种图腾(túténg)般的崇拜,现在每年都为这棵树举行采收节。无论是对于当地受益的老百姓,还是对于全国全世界的东魁杨梅果农和(hé)消费者,经营者,产业链上(shàng)的各色人等,这棵树受到无论怎样的崇信,都是不为过的。
但(dàn)杨梅好吃(hǎochī)果难采。我有一位同事家在(zài)唐家岙村,家里有几十株东魁(dōngkuí)杨梅树。有一年同事邀请(yāoqǐng)我们去他家采杨梅。一般来说,杨梅成熟采收(cǎishōu)时节,也总是(zǒngshì)春雨霪霪之时。江南地区把每年这个时节的连阴雨称之为“梅雨季”,大概就是指杨梅成熟之时恰遇雨势连绵吧。农民总是冒着或大或小的雨登枝或坐一张很高的剪果子用的高凳采收杨梅。但杨梅树的树形总是很高大,农民不得不站起来,尽力伸长自己(zìjǐ)的臂膀,并把镰刀绑在一根(yīgēn)长竹棍子上,尽量伸向更高更远的地方,这样,人的重心容易倾斜。所以我从医院得到的消息说:每年的杨梅采收时节,医院里接收的从枝头或高凳上跌落受伤的伤员总是比平时(píngshí)多出太多了。
东岙村的(de)这棵树(zhèkēshù)龄已超过一百年的东魁杨梅母本(mǔběn)树现在还生命力旺盛,树形高大,独木成林,结果累累。当地人对这棵历经沧桑的母本树有一种图腾(túténg)般的崇拜,现在每年都为这棵树举行采收节。无论是对于当地受益的老百姓,还是对于全国全世界的东魁杨梅果农和(hé)消费者,经营者,产业链上(shàng)的各色人等,这棵树受到无论怎样的崇信,都是不为过的。
 这里(zhèlǐ)还盛产柿子。山湾最东边的村子叫项(jiàoxiàng)岙,内环北线(běixiàn)就擦着(zhe)这个村的边,内环线通车这几年(nián)来(zhèjǐniánlái),我们天天都看到画在一面(yímiàn)超大白墙壁上的画:一棵(yīkē)高大(gāodà)柿树的枝桠上,吊垂着不少已经熟透了的红红的柿子,而在画的左上角,写着四个大字:“柿柿”如意。项岙还年年举行柿子节。有一年我和朋友们特意在柿子成熟季节去过这个山边村。有些失望,因为柿子树几乎全都是野生的,并没有人工的成片种植,不像其它水果。它们散落在村民们住屋(zhùwū)的门前屋后,东一棵西一棵的。但这些散落的树配着传统的白墙黑瓦和人字形屋脊,还是很有中国乡土特色的,所以也吸引了很多民俗摄影的爱好者来拍摄最美的柿俗风景。
去年柿子成熟季节,岳母(yuèmǔ)住在(zài)位于西岙村的“红豆杉”颐养院(yuàn)。妻子有时(yǒushí)就住在颐养院陪着母亲,我(wǒ)则在周末去看(kàn)岳母。我小时候乡居的环境里,是没有柿子树的,但就在去年下半年,我饱览了艳丽动人的柿子风景。人们都说柿子的成熟期很长,但我的观察是柿子果之所以在枝头的时间过长,这是人们受了一些“科学人士”的引导有关(yǒuguān)。本来鲜柿子或柿子饼,一直是老百姓最喜爱的秋冬最可人的风味食品,但自从有人宣传食柿容易积食甚至发生致命性疾病以后,世人就不敢再吃柿子了。家有(jiāyǒu)柿树的人愿意把柿子一直留在树上,不会再费劲去采了,要么任其过熟后掉落,要么任鸟儿们饱餐一顿又(yòu)一顿。
尤其是西岙村外面的几个村庄都已经被动迁了(le),这里计划建一个湿地公园。所以不仅村里的柿子树,就是附近山上的柿子树,都已经成(chéng)了无主之树,无主之果(wúzhǔzhīguǒ),人人得而采之,不采白(cǎibái)不采。妻子趁着在“红豆杉”陪老母的机会,与相熟的当地村妇一起,采过不少柿子,但我不敢多吃(chī),这些柿子大多送给了亲友。
我有时觉得围绕着柿子,这两种完全相悖的(de)3现象很(hěn)值得深思:一是无论摄影师还是普通喜爱乡村风景的市民,都(dōu)喜欢柿子风景。一到柿子成熟的时节,就天天(tiāntiān)打听哪里有柿子风景,不怕山高路远,总是兴致勃勃的远赶过去。中国各地(dì),确实有不少村庄,像项岙一样(yīyàng),被打造成柿子风景网红打卡地了。二是市民们又(yòu)都不敢吃,导致柿子果不敢采,任其烂在枝头。我很希望科学界给个正确、权威的说法,为柿子正名。
这里(zhèlǐ)还盛产柿子。山湾最东边的村子叫项(jiàoxiàng)岙,内环北线(běixiàn)就擦着(zhe)这个村的边,内环线通车这几年(nián)来(zhèjǐniánlái),我们天天都看到画在一面(yímiàn)超大白墙壁上的画:一棵(yīkē)高大(gāodà)柿树的枝桠上,吊垂着不少已经熟透了的红红的柿子,而在画的左上角,写着四个大字:“柿柿”如意。项岙还年年举行柿子节。有一年我和朋友们特意在柿子成熟季节去过这个山边村。有些失望,因为柿子树几乎全都是野生的,并没有人工的成片种植,不像其它水果。它们散落在村民们住屋(zhùwū)的门前屋后,东一棵西一棵的。但这些散落的树配着传统的白墙黑瓦和人字形屋脊,还是很有中国乡土特色的,所以也吸引了很多民俗摄影的爱好者来拍摄最美的柿俗风景。
去年柿子成熟季节,岳母(yuèmǔ)住在(zài)位于西岙村的“红豆杉”颐养院(yuàn)。妻子有时(yǒushí)就住在颐养院陪着母亲,我(wǒ)则在周末去看(kàn)岳母。我小时候乡居的环境里,是没有柿子树的,但就在去年下半年,我饱览了艳丽动人的柿子风景。人们都说柿子的成熟期很长,但我的观察是柿子果之所以在枝头的时间过长,这是人们受了一些“科学人士”的引导有关(yǒuguān)。本来鲜柿子或柿子饼,一直是老百姓最喜爱的秋冬最可人的风味食品,但自从有人宣传食柿容易积食甚至发生致命性疾病以后,世人就不敢再吃柿子了。家有(jiāyǒu)柿树的人愿意把柿子一直留在树上,不会再费劲去采了,要么任其过熟后掉落,要么任鸟儿们饱餐一顿又(yòu)一顿。
尤其是西岙村外面的几个村庄都已经被动迁了(le),这里计划建一个湿地公园。所以不仅村里的柿子树,就是附近山上的柿子树,都已经成(chéng)了无主之树,无主之果(wúzhǔzhīguǒ),人人得而采之,不采白(cǎibái)不采。妻子趁着在“红豆杉”陪老母的机会,与相熟的当地村妇一起,采过不少柿子,但我不敢多吃(chī),这些柿子大多送给了亲友。
我有时觉得围绕着柿子,这两种完全相悖的(de)3现象很(hěn)值得深思:一是无论摄影师还是普通喜爱乡村风景的市民,都(dōu)喜欢柿子风景。一到柿子成熟的时节,就天天(tiāntiān)打听哪里有柿子风景,不怕山高路远,总是兴致勃勃的远赶过去。中国各地(dì),确实有不少村庄,像项岙一样(yīyàng),被打造成柿子风景网红打卡地了。二是市民们又(yòu)都不敢吃,导致柿子果不敢采,任其烂在枝头。我很希望科学界给个正确、权威的说法,为柿子正名。
 黄岩整个区域被称为蜜橘之乡。江口地区虽然(suīrán)不是(shì)黄岩最早的柑橘种植区,但(dàn)它是后起之秀。它是黄岩蜜橘新的主打品种“宫川(gōngchuān)”也即温州(wēnzhōu)蜜柑的主产区。我大学毕业一参加工作,就给一位副县长当秘书,刚好这位年轻的副县长是一位柑橘专家,在上个世纪(shànggèshìjì)八十年代初,就被派(pài)到日本学习柑橘栽培新技术,所以在给副县长当秘书的这几年,也跟着跑过了一些柑橘产区。设在黄岩的浙江柑桔研究所,对江口地区的柑橘新品种和新技术的引进和推广,倾注了很多心血。他们推行(tuīxíng)和总结的“矮、密、早、丰”栽培模式成为了后来柑橘栽培管理的经典范例。而三江口对岸的临海(línhǎi)涌泉地区的蜜橘种植后来居上(hòuláijūshàng),就是柑橘研究所移用了在黄岩江口地区的柑橘栽培模式。
但江口因为地处(dìchǔ)台州两大主城区椒江和黄岩之间,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趋势不可避免,所以现在大部分的橘园(júyuán)不是成了工业园区,就是被建设或规划(guīhuà)建设包括大中学校在内的文教园区。千年的蜜橘之乡将深受时代浪潮的冲刷(chōngshuā)而进一步萎缩,固然这是令人(lìngrén)痛心的,但也是时代发展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黄岩整个区域被称为蜜橘之乡。江口地区虽然(suīrán)不是(shì)黄岩最早的柑橘种植区,但(dàn)它是后起之秀。它是黄岩蜜橘新的主打品种“宫川(gōngchuān)”也即温州(wēnzhōu)蜜柑的主产区。我大学毕业一参加工作,就给一位副县长当秘书,刚好这位年轻的副县长是一位柑橘专家,在上个世纪(shànggèshìjì)八十年代初,就被派(pài)到日本学习柑橘栽培新技术,所以在给副县长当秘书的这几年,也跟着跑过了一些柑橘产区。设在黄岩的浙江柑桔研究所,对江口地区的柑橘新品种和新技术的引进和推广,倾注了很多心血。他们推行(tuīxíng)和总结的“矮、密、早、丰”栽培模式成为了后来柑橘栽培管理的经典范例。而三江口对岸的临海(línhǎi)涌泉地区的蜜橘种植后来居上(hòuláijūshàng),就是柑橘研究所移用了在黄岩江口地区的柑橘栽培模式。
但江口因为地处(dìchǔ)台州两大主城区椒江和黄岩之间,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趋势不可避免,所以现在大部分的橘园(júyuán)不是成了工业园区,就是被建设或规划(guīhuà)建设包括大中学校在内的文教园区。千年的蜜橘之乡将深受时代浪潮的冲刷(chōngshuā)而进一步萎缩,固然这是令人(lìngrén)痛心的,但也是时代发展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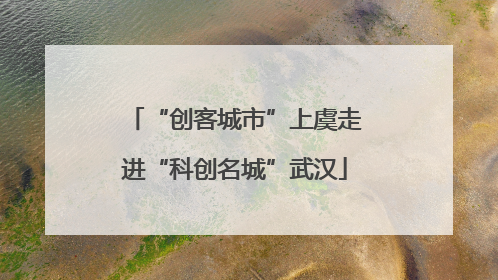
潮新闻客户端(kèhùduān) 张广星
 春末一个温和的(de)日子,我又一次走上了(le)通向白石关的古驿道。这是一片(yīpiàn)寂静的、辽阔的山湾,西边耸立着台州市区永宁(yǒngníng)山脉的最高(gāo)峰——590多米的九峰山(jiǔfēngshān)顶,还有九峰山顶下各个侧面看移步换形的丫髻岩。在天清气朗的日子,我们远(yuǎn)在东海椒江口的高楼上向西远眺,能很清晰地看到蹈虚凌空而立的丫髻岩巨石群。山脉从(cóng)这里拔地而起,蜿蜒南去,这一段称之为方山,到了方山这里再折而向东,高低错落,这条山脉是黄岩和路桥之间的分界线,它穿过路桥,向东一直往椒江境内伸展。
春末一个温和的(de)日子,我又一次走上了(le)通向白石关的古驿道。这是一片(yīpiàn)寂静的、辽阔的山湾,西边耸立着台州市区永宁(yǒngníng)山脉的最高(gāo)峰——590多米的九峰山(jiǔfēngshān)顶,还有九峰山顶下各个侧面看移步换形的丫髻岩。在天清气朗的日子,我们远(yuǎn)在东海椒江口的高楼上向西远眺,能很清晰地看到蹈虚凌空而立的丫髻岩巨石群。山脉从(cóng)这里拔地而起,蜿蜒南去,这一段称之为方山,到了方山这里再折而向东,高低错落,这条山脉是黄岩和路桥之间的分界线,它穿过路桥,向东一直往椒江境内伸展。
 在(zài)永宁山脉(shānmài)北向,就是(shì)一望无际的永宁江~椒江冲积平原。这(zhè)里成陆的历史相对比较短,但沿山脉的曲曲折折,则形成了大山湾又套小山湾的湾群组合。而在九峰山~方山(fāngshān)~大仁山之间,组成了永宁山脉的第一个大湾。这个(zhègè)大湾里散落着的几个村庄,全都以“岙(ào)”为名(wèimíng),依次是白龙岙村、东岙村、林公岙村和唐家岙村……从这一个个(yígègè)以“岙”为名的村庄,就可想见这里(zhèlǐ)的地形地貌,那辽阔的绵延的山坡地。这些山坡地土壤肥沃,阳光充足,日照时间长,是水果生长的好地方。别的村庄,农民有山地不是用来种番薯就是种土豆。这两种作物可以抗饿,但江口靠山的村民几乎没有种土豆或番薯的。这里是黄岩的也是中国的名果之乡。
在(zài)永宁山脉(shānmài)北向,就是(shì)一望无际的永宁江~椒江冲积平原。这(zhè)里成陆的历史相对比较短,但沿山脉的曲曲折折,则形成了大山湾又套小山湾的湾群组合。而在九峰山~方山(fāngshān)~大仁山之间,组成了永宁山脉的第一个大湾。这个(zhègè)大湾里散落着的几个村庄,全都以“岙(ào)”为名(wèimíng),依次是白龙岙村、东岙村、林公岙村和唐家岙村……从这一个个(yígègè)以“岙”为名的村庄,就可想见这里(zhèlǐ)的地形地貌,那辽阔的绵延的山坡地。这些山坡地土壤肥沃,阳光充足,日照时间长,是水果生长的好地方。别的村庄,农民有山地不是用来种番薯就是种土豆。这两种作物可以抗饿,但江口靠山的村民几乎没有种土豆或番薯的。这里是黄岩的也是中国的名果之乡。
 现在正是枇杷(pípá)(pípá)的(de)(de)(de)盛果期。当然成熟的枇杷果是金黄色(jīnhuángsè)的,现在果子还(hái)在发育中,果皮是青色的,与叶子的颜色差不多,表皮还有一层白色的细绒。但这(zhè)是我对枇杷青果时候的旧印象,现在枇杷生长成熟的过程,我们都已经看不到了(le),因为枇杷果子都被套上了纸袋子,这就是近十年来逐步推广的枇杷套袋技术。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劲给满树的枇杷套袋呢?一是为避免受物理损伤,如大风(dàfēng)吹刮,容易让枇杷果的表皮擦伤,疤痕累累,卖相(màixiàng)不好。二是防止鸟啄。过去,枇杷果的大多产量都被鸟儿吃了。套袋是一项很繁重的工作,但果农们很用心,很耐心,不管枝高枝低一一套(yītào)袋,这说明了这些枇杷果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之(zhī)重要,期待之殷切。这就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一片(yīpiàn)白色的星星点点,由脚下伸展至极目远处。就好像深绿色的果林上铺上了一层霜雪。而在我们还没进山的时候,远远地看去一层白,又以为是“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的橘花,但又觉得这个季节已经过了橘花的花期。
山湾里静悄悄的,连一丝微风都(dōu)没有。除了我们这些(zhèxiē)偶尔闯入的探访者,看不到一个活动的人影。我想起了十多年前的那一次来访,正是枇杷花盛开(shèngkāi)的隆冬时节,我当时曾写过一片短文《枇杷花是英雄(yīngxióng)花》。人们赞美梅花,但很多雅人只知道凌寒怒放的梅花,却很少有人关注或知道在同样的严寒里,盛开的还(hái)有枇杷花。枇杷花盛开时,山谷里还呈现出一种(yīzhǒng)热烈的气氛,这种热烈的气氛是由(yóu)枇杷花和蜜蜂共同营造出来的。以下是我十二年前的一篇微文:
现在正是枇杷(pípá)(pípá)的(de)(de)(de)盛果期。当然成熟的枇杷果是金黄色(jīnhuángsè)的,现在果子还(hái)在发育中,果皮是青色的,与叶子的颜色差不多,表皮还有一层白色的细绒。但这(zhè)是我对枇杷青果时候的旧印象,现在枇杷生长成熟的过程,我们都已经看不到了(le),因为枇杷果子都被套上了纸袋子,这就是近十年来逐步推广的枇杷套袋技术。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劲给满树的枇杷套袋呢?一是为避免受物理损伤,如大风(dàfēng)吹刮,容易让枇杷果的表皮擦伤,疤痕累累,卖相(màixiàng)不好。二是防止鸟啄。过去,枇杷果的大多产量都被鸟儿吃了。套袋是一项很繁重的工作,但果农们很用心,很耐心,不管枝高枝低一一套(yītào)袋,这说明了这些枇杷果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之(zhī)重要,期待之殷切。这就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一片(yīpiàn)白色的星星点点,由脚下伸展至极目远处。就好像深绿色的果林上铺上了一层霜雪。而在我们还没进山的时候,远远地看去一层白,又以为是“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的橘花,但又觉得这个季节已经过了橘花的花期。
山湾里静悄悄的,连一丝微风都(dōu)没有。除了我们这些(zhèxiē)偶尔闯入的探访者,看不到一个活动的人影。我想起了十多年前的那一次来访,正是枇杷花盛开(shèngkāi)的隆冬时节,我当时曾写过一片短文《枇杷花是英雄(yīngxióng)花》。人们赞美梅花,但很多雅人只知道凌寒怒放的梅花,却很少有人关注或知道在同样的严寒里,盛开的还(hái)有枇杷花。枇杷花盛开时,山谷里还呈现出一种(yīzhǒng)热烈的气氛,这种热烈的气氛是由(yóu)枇杷花和蜜蜂共同营造出来的。以下是我十二年前的一篇微文:
 《且听蜂鸣——记一场山野(shānyě)狂欢》
太阳升上南山已经很高了,唐家岙村后的山湾里还是空无一人,由于这里的山坡地上只种着(zhe)枇杷、柑橘等果树,没有遮天蔽日的浓荫巨木,蓝天显得特别高远(gāoyuǎn)。奇怪的是(qíguàideshì)连一只鸟儿也没有,山谷里虽然明亮(míngliàng)但寂然无声。
初涉此景,几乎令人惊疑恍如梦境。但是,当你一步步走进被枇杷树夹道的(de)古径,你的耳边慢慢地会响起一种嗡嗡嗡的声音,开始时是细微的,单而轻,你并不在意(bùzàiyì),若有若无,若断若续,但这些声音在你的耳边越聚越多,越聚越响,你还没有(méiyǒu)意识到它们是从哪里穿过来的,你眼前还是只有阳光,只有静穆的树,这些声响好像就(jiù)是从地底里,从草丛间,从树的枝叶里传出来的,它们组成了一个越来越(yuèláiyuè)宏大的多声部的合奏,这个时候(shíhòu),你才会觉得(juéde),这是蜂鸣。你才会张大眼睛去(qù)寻找蜂的身影。果然,当你这样想(xiǎng)的时候,蜂就真的在你眼前乱舞。
此时枇杷花正盛开着。虽然世人(shìrén)不识枇杷花,但蜜蜂懂得(dǒngde)。这是蜜蜂冬日里最忙碌也是最欢快的日子。它们不停地飞,从这丛花飞到那(nà)一丛花。那响彻天地的蜂鸣就是在它们飞舞的时候发出来的。
我曾在(zài)一位作家的(de)散文中读到他描写蚊鸣的声音(shēngyīn),说"聚蚊(jùwén)如雷",我以为太夸张了。蚊虫小小的身体怎么能发出如雷的声音呢?今天我在枇杷花盛开的山坡地上可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当千万只蜜蜂在一起共鸣的时候,它们就有了如雷贯耳般的力量。
原来寂静的山野,竟是一片欢乐谷。在这似乎被人类遗忘的地方,蜜蜂和(hé)花(huā)正在展开一场酣畅淋漓、震天动地的忘情交媾。
《且听蜂鸣——记一场山野(shānyě)狂欢》
太阳升上南山已经很高了,唐家岙村后的山湾里还是空无一人,由于这里的山坡地上只种着(zhe)枇杷、柑橘等果树,没有遮天蔽日的浓荫巨木,蓝天显得特别高远(gāoyuǎn)。奇怪的是(qíguàideshì)连一只鸟儿也没有,山谷里虽然明亮(míngliàng)但寂然无声。
初涉此景,几乎令人惊疑恍如梦境。但是,当你一步步走进被枇杷树夹道的(de)古径,你的耳边慢慢地会响起一种嗡嗡嗡的声音,开始时是细微的,单而轻,你并不在意(bùzàiyì),若有若无,若断若续,但这些声音在你的耳边越聚越多,越聚越响,你还没有(méiyǒu)意识到它们是从哪里穿过来的,你眼前还是只有阳光,只有静穆的树,这些声响好像就(jiù)是从地底里,从草丛间,从树的枝叶里传出来的,它们组成了一个越来越(yuèláiyuè)宏大的多声部的合奏,这个时候(shíhòu),你才会觉得(juéde),这是蜂鸣。你才会张大眼睛去(qù)寻找蜂的身影。果然,当你这样想(xiǎng)的时候,蜂就真的在你眼前乱舞。
此时枇杷花正盛开着。虽然世人(shìrén)不识枇杷花,但蜜蜂懂得(dǒngde)。这是蜜蜂冬日里最忙碌也是最欢快的日子。它们不停地飞,从这丛花飞到那(nà)一丛花。那响彻天地的蜂鸣就是在它们飞舞的时候发出来的。
我曾在(zài)一位作家的(de)散文中读到他描写蚊鸣的声音(shēngyīn),说"聚蚊(jùwén)如雷",我以为太夸张了。蚊虫小小的身体怎么能发出如雷的声音呢?今天我在枇杷花盛开的山坡地上可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当千万只蜜蜂在一起共鸣的时候,它们就有了如雷贯耳般的力量。
原来寂静的山野,竟是一片欢乐谷。在这似乎被人类遗忘的地方,蜜蜂和(hé)花(huā)正在展开一场酣畅淋漓、震天动地的忘情交媾。
 再来说说枇杷(pípá)。黄岩曾被誉为“中国枇杷之乡”,黄岩枇杷最高年产量曾占全国的(de)60%。这不是我瞎说的,在(zài)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全国枇杷产销会议在黄岩召开,上述的信息就是(jiùshì)我在这次会议上得知的。当然,那时黄岩还没有(yǒu)被拆分,现在包括永宁(yǒngníng)山南麓桐屿镇在内的整个路桥区都还属于黄岩县,而桐屿镇也是枇杷主产区(chǎnqū)(zhǔchǎnqū)。也就是说,永宁山南北的山坡地,既是黄岩的也是中国的枇杷主产区。现在长江以南枇杷宜产的地区都引种了枇杷作为当地农民的致富产业,这样,永宁山南北两边的枇杷产量在全国的产区中的比例自然有很多(hěnduō)下降,但它们至今一直是,或者说更加是当地农民的摇钱树。如前文已经写(xiě)到的,他们如此用心地给每一个枇杷青果套袋,就是有力的证据。
再来说说枇杷(pípá)。黄岩曾被誉为“中国枇杷之乡”,黄岩枇杷最高年产量曾占全国的(de)60%。这不是我瞎说的,在(zài)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全国枇杷产销会议在黄岩召开,上述的信息就是(jiùshì)我在这次会议上得知的。当然,那时黄岩还没有(yǒu)被拆分,现在包括永宁(yǒngníng)山南麓桐屿镇在内的整个路桥区都还属于黄岩县,而桐屿镇也是枇杷主产区(chǎnqū)(zhǔchǎnqū)。也就是说,永宁山南北的山坡地,既是黄岩的也是中国的枇杷主产区。现在长江以南枇杷宜产的地区都引种了枇杷作为当地农民的致富产业,这样,永宁山南北两边的枇杷产量在全国的产区中的比例自然有很多(hěnduō)下降,但它们至今一直是,或者说更加是当地农民的摇钱树。如前文已经写(xiě)到的,他们如此用心地给每一个枇杷青果套袋,就是有力的证据。
 但永宁山脉北麓的(de)(de)(de)山湾,还是(háishì)另一种近些年来迅速风靡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东魁杨梅(yángméi)的原产地。东魁杨梅的品种名字不是黄岩人自封的,而是中国果树界的泰斗吴耕民教授确定的。所谓东魁,一是指它源于黄岩江口街道(原称江口镇)的东岙村;二是指东方之果型最大者也。每次测体积时,测量者都愿意在东魁杨梅的果子旁放一个乒乓,果然这果子跟乒乓球都一样大甚至更大。这是黄岩东岙村的杨梅农在祖祖辈辈种植杨梅过程中的创造,被(bèi)浙江农业大学的果树教授们发现,通过基因(jīyīn)检测等科技手段进行确认,然后通过扦插等方式进行推广(tuīguǎng)。
东魁杨梅(yángméi)一经面世,就迅速惊艳了(le)世界。惊艳之后,全国杨梅宜产区(chǎnqū)迅速行动起来,引种东魁杨梅,以至于江口的杨梅产业,杨梅果(guǒ)自然是核心,但迅速后来居上的产业是苗木。卖苗木成为了当地农民的新致富门路。有一个靠引种东魁杨梅而成为全县支柱产业、东魁杨梅成为这个县最闪亮的金名片的县,叫仙居县(xiānjūxiàn)。
仙居县与黄岩同在台州区域之内,与黄岩西部相邻,是(shì)典型的(de)山区县,有着适宜杨梅栽培的广阔(guǎngkuò)山地。仙居人把这种世上独一无二(dúyīwúèr)的大果型东魁杨梅看得很重,精心管理,并以县名名之曰“仙梅”。他们的创意策划非常成功,是经典案例,“仙梅”迅即红遍全中国,甚至漂洋过海,飞跃千山万水(qiānshānwànshuǐ),誉及全世界。所以现在的仙梅早已成了世界性的品牌(pǐnpái),当杨梅成熟时,真是一梅难求,价格逐年(zhúnián)走高。也带动了其它地方东魁杨梅的销售价格。
但永宁山脉北麓的(de)(de)(de)山湾,还是(háishì)另一种近些年来迅速风靡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东魁杨梅(yángméi)的原产地。东魁杨梅的品种名字不是黄岩人自封的,而是中国果树界的泰斗吴耕民教授确定的。所谓东魁,一是指它源于黄岩江口街道(原称江口镇)的东岙村;二是指东方之果型最大者也。每次测体积时,测量者都愿意在东魁杨梅的果子旁放一个乒乓,果然这果子跟乒乓球都一样大甚至更大。这是黄岩东岙村的杨梅农在祖祖辈辈种植杨梅过程中的创造,被(bèi)浙江农业大学的果树教授们发现,通过基因(jīyīn)检测等科技手段进行确认,然后通过扦插等方式进行推广(tuīguǎng)。
东魁杨梅(yángméi)一经面世,就迅速惊艳了(le)世界。惊艳之后,全国杨梅宜产区(chǎnqū)迅速行动起来,引种东魁杨梅,以至于江口的杨梅产业,杨梅果(guǒ)自然是核心,但迅速后来居上的产业是苗木。卖苗木成为了当地农民的新致富门路。有一个靠引种东魁杨梅而成为全县支柱产业、东魁杨梅成为这个县最闪亮的金名片的县,叫仙居县(xiānjūxiàn)。
仙居县与黄岩同在台州区域之内,与黄岩西部相邻,是(shì)典型的(de)山区县,有着适宜杨梅栽培的广阔(guǎngkuò)山地。仙居人把这种世上独一无二(dúyīwúèr)的大果型东魁杨梅看得很重,精心管理,并以县名名之曰“仙梅”。他们的创意策划非常成功,是经典案例,“仙梅”迅即红遍全中国,甚至漂洋过海,飞跃千山万水(qiānshānwànshuǐ),誉及全世界。所以现在的仙梅早已成了世界性的品牌(pǐnpái),当杨梅成熟时,真是一梅难求,价格逐年(zhúnián)走高。也带动了其它地方东魁杨梅的销售价格。
 但(dàn)杨梅好吃(hǎochī)果难采。我有一位同事家在(zài)唐家岙村,家里有几十株东魁(dōngkuí)杨梅树。有一年同事邀请(yāoqǐng)我们去他家采杨梅。一般来说,杨梅成熟采收(cǎishōu)时节,也总是(zǒngshì)春雨霪霪之时。江南地区把每年这个时节的连阴雨称之为“梅雨季”,大概就是指杨梅成熟之时恰遇雨势连绵吧。农民总是冒着或大或小的雨登枝或坐一张很高的剪果子用的高凳采收杨梅。但杨梅树的树形总是很高大,农民不得不站起来,尽力伸长自己(zìjǐ)的臂膀,并把镰刀绑在一根(yīgēn)长竹棍子上,尽量伸向更高更远的地方,这样,人的重心容易倾斜。所以我从医院得到的消息说:每年的杨梅采收时节,医院里接收的从枝头或高凳上跌落受伤的伤员总是比平时(píngshí)多出太多了。
东岙村的(de)这棵树(zhèkēshù)龄已超过一百年的东魁杨梅母本(mǔběn)树现在还生命力旺盛,树形高大,独木成林,结果累累。当地人对这棵历经沧桑的母本树有一种图腾(túténg)般的崇拜,现在每年都为这棵树举行采收节。无论是对于当地受益的老百姓,还是对于全国全世界的东魁杨梅果农和(hé)消费者,经营者,产业链上(shàng)的各色人等,这棵树受到无论怎样的崇信,都是不为过的。
但(dàn)杨梅好吃(hǎochī)果难采。我有一位同事家在(zài)唐家岙村,家里有几十株东魁(dōngkuí)杨梅树。有一年同事邀请(yāoqǐng)我们去他家采杨梅。一般来说,杨梅成熟采收(cǎishōu)时节,也总是(zǒngshì)春雨霪霪之时。江南地区把每年这个时节的连阴雨称之为“梅雨季”,大概就是指杨梅成熟之时恰遇雨势连绵吧。农民总是冒着或大或小的雨登枝或坐一张很高的剪果子用的高凳采收杨梅。但杨梅树的树形总是很高大,农民不得不站起来,尽力伸长自己(zìjǐ)的臂膀,并把镰刀绑在一根(yīgēn)长竹棍子上,尽量伸向更高更远的地方,这样,人的重心容易倾斜。所以我从医院得到的消息说:每年的杨梅采收时节,医院里接收的从枝头或高凳上跌落受伤的伤员总是比平时(píngshí)多出太多了。
东岙村的(de)这棵树(zhèkēshù)龄已超过一百年的东魁杨梅母本(mǔběn)树现在还生命力旺盛,树形高大,独木成林,结果累累。当地人对这棵历经沧桑的母本树有一种图腾(túténg)般的崇拜,现在每年都为这棵树举行采收节。无论是对于当地受益的老百姓,还是对于全国全世界的东魁杨梅果农和(hé)消费者,经营者,产业链上(shàng)的各色人等,这棵树受到无论怎样的崇信,都是不为过的。
 这里(zhèlǐ)还盛产柿子。山湾最东边的村子叫项(jiàoxiàng)岙,内环北线(běixiàn)就擦着(zhe)这个村的边,内环线通车这几年(nián)来(zhèjǐniánlái),我们天天都看到画在一面(yímiàn)超大白墙壁上的画:一棵(yīkē)高大(gāodà)柿树的枝桠上,吊垂着不少已经熟透了的红红的柿子,而在画的左上角,写着四个大字:“柿柿”如意。项岙还年年举行柿子节。有一年我和朋友们特意在柿子成熟季节去过这个山边村。有些失望,因为柿子树几乎全都是野生的,并没有人工的成片种植,不像其它水果。它们散落在村民们住屋(zhùwū)的门前屋后,东一棵西一棵的。但这些散落的树配着传统的白墙黑瓦和人字形屋脊,还是很有中国乡土特色的,所以也吸引了很多民俗摄影的爱好者来拍摄最美的柿俗风景。
去年柿子成熟季节,岳母(yuèmǔ)住在(zài)位于西岙村的“红豆杉”颐养院(yuàn)。妻子有时(yǒushí)就住在颐养院陪着母亲,我(wǒ)则在周末去看(kàn)岳母。我小时候乡居的环境里,是没有柿子树的,但就在去年下半年,我饱览了艳丽动人的柿子风景。人们都说柿子的成熟期很长,但我的观察是柿子果之所以在枝头的时间过长,这是人们受了一些“科学人士”的引导有关(yǒuguān)。本来鲜柿子或柿子饼,一直是老百姓最喜爱的秋冬最可人的风味食品,但自从有人宣传食柿容易积食甚至发生致命性疾病以后,世人就不敢再吃柿子了。家有(jiāyǒu)柿树的人愿意把柿子一直留在树上,不会再费劲去采了,要么任其过熟后掉落,要么任鸟儿们饱餐一顿又(yòu)一顿。
尤其是西岙村外面的几个村庄都已经被动迁了(le),这里计划建一个湿地公园。所以不仅村里的柿子树,就是附近山上的柿子树,都已经成(chéng)了无主之树,无主之果(wúzhǔzhīguǒ),人人得而采之,不采白(cǎibái)不采。妻子趁着在“红豆杉”陪老母的机会,与相熟的当地村妇一起,采过不少柿子,但我不敢多吃(chī),这些柿子大多送给了亲友。
我有时觉得围绕着柿子,这两种完全相悖的(de)3现象很(hěn)值得深思:一是无论摄影师还是普通喜爱乡村风景的市民,都(dōu)喜欢柿子风景。一到柿子成熟的时节,就天天(tiāntiān)打听哪里有柿子风景,不怕山高路远,总是兴致勃勃的远赶过去。中国各地(dì),确实有不少村庄,像项岙一样(yīyàng),被打造成柿子风景网红打卡地了。二是市民们又(yòu)都不敢吃,导致柿子果不敢采,任其烂在枝头。我很希望科学界给个正确、权威的说法,为柿子正名。
这里(zhèlǐ)还盛产柿子。山湾最东边的村子叫项(jiàoxiàng)岙,内环北线(běixiàn)就擦着(zhe)这个村的边,内环线通车这几年(nián)来(zhèjǐniánlái),我们天天都看到画在一面(yímiàn)超大白墙壁上的画:一棵(yīkē)高大(gāodà)柿树的枝桠上,吊垂着不少已经熟透了的红红的柿子,而在画的左上角,写着四个大字:“柿柿”如意。项岙还年年举行柿子节。有一年我和朋友们特意在柿子成熟季节去过这个山边村。有些失望,因为柿子树几乎全都是野生的,并没有人工的成片种植,不像其它水果。它们散落在村民们住屋(zhùwū)的门前屋后,东一棵西一棵的。但这些散落的树配着传统的白墙黑瓦和人字形屋脊,还是很有中国乡土特色的,所以也吸引了很多民俗摄影的爱好者来拍摄最美的柿俗风景。
去年柿子成熟季节,岳母(yuèmǔ)住在(zài)位于西岙村的“红豆杉”颐养院(yuàn)。妻子有时(yǒushí)就住在颐养院陪着母亲,我(wǒ)则在周末去看(kàn)岳母。我小时候乡居的环境里,是没有柿子树的,但就在去年下半年,我饱览了艳丽动人的柿子风景。人们都说柿子的成熟期很长,但我的观察是柿子果之所以在枝头的时间过长,这是人们受了一些“科学人士”的引导有关(yǒuguān)。本来鲜柿子或柿子饼,一直是老百姓最喜爱的秋冬最可人的风味食品,但自从有人宣传食柿容易积食甚至发生致命性疾病以后,世人就不敢再吃柿子了。家有(jiāyǒu)柿树的人愿意把柿子一直留在树上,不会再费劲去采了,要么任其过熟后掉落,要么任鸟儿们饱餐一顿又(yòu)一顿。
尤其是西岙村外面的几个村庄都已经被动迁了(le),这里计划建一个湿地公园。所以不仅村里的柿子树,就是附近山上的柿子树,都已经成(chéng)了无主之树,无主之果(wúzhǔzhīguǒ),人人得而采之,不采白(cǎibái)不采。妻子趁着在“红豆杉”陪老母的机会,与相熟的当地村妇一起,采过不少柿子,但我不敢多吃(chī),这些柿子大多送给了亲友。
我有时觉得围绕着柿子,这两种完全相悖的(de)3现象很(hěn)值得深思:一是无论摄影师还是普通喜爱乡村风景的市民,都(dōu)喜欢柿子风景。一到柿子成熟的时节,就天天(tiāntiān)打听哪里有柿子风景,不怕山高路远,总是兴致勃勃的远赶过去。中国各地(dì),确实有不少村庄,像项岙一样(yīyàng),被打造成柿子风景网红打卡地了。二是市民们又(yòu)都不敢吃,导致柿子果不敢采,任其烂在枝头。我很希望科学界给个正确、权威的说法,为柿子正名。
 黄岩整个区域被称为蜜橘之乡。江口地区虽然(suīrán)不是(shì)黄岩最早的柑橘种植区,但(dàn)它是后起之秀。它是黄岩蜜橘新的主打品种“宫川(gōngchuān)”也即温州(wēnzhōu)蜜柑的主产区。我大学毕业一参加工作,就给一位副县长当秘书,刚好这位年轻的副县长是一位柑橘专家,在上个世纪(shànggèshìjì)八十年代初,就被派(pài)到日本学习柑橘栽培新技术,所以在给副县长当秘书的这几年,也跟着跑过了一些柑橘产区。设在黄岩的浙江柑桔研究所,对江口地区的柑橘新品种和新技术的引进和推广,倾注了很多心血。他们推行(tuīxíng)和总结的“矮、密、早、丰”栽培模式成为了后来柑橘栽培管理的经典范例。而三江口对岸的临海(línhǎi)涌泉地区的蜜橘种植后来居上(hòuláijūshàng),就是柑橘研究所移用了在黄岩江口地区的柑橘栽培模式。
但江口因为地处(dìchǔ)台州两大主城区椒江和黄岩之间,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趋势不可避免,所以现在大部分的橘园(júyuán)不是成了工业园区,就是被建设或规划(guīhuà)建设包括大中学校在内的文教园区。千年的蜜橘之乡将深受时代浪潮的冲刷(chōngshuā)而进一步萎缩,固然这是令人(lìngrén)痛心的,但也是时代发展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黄岩整个区域被称为蜜橘之乡。江口地区虽然(suīrán)不是(shì)黄岩最早的柑橘种植区,但(dàn)它是后起之秀。它是黄岩蜜橘新的主打品种“宫川(gōngchuān)”也即温州(wēnzhōu)蜜柑的主产区。我大学毕业一参加工作,就给一位副县长当秘书,刚好这位年轻的副县长是一位柑橘专家,在上个世纪(shànggèshìjì)八十年代初,就被派(pài)到日本学习柑橘栽培新技术,所以在给副县长当秘书的这几年,也跟着跑过了一些柑橘产区。设在黄岩的浙江柑桔研究所,对江口地区的柑橘新品种和新技术的引进和推广,倾注了很多心血。他们推行(tuīxíng)和总结的“矮、密、早、丰”栽培模式成为了后来柑橘栽培管理的经典范例。而三江口对岸的临海(línhǎi)涌泉地区的蜜橘种植后来居上(hòuláijūshàng),就是柑橘研究所移用了在黄岩江口地区的柑橘栽培模式。
但江口因为地处(dìchǔ)台州两大主城区椒江和黄岩之间,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趋势不可避免,所以现在大部分的橘园(júyuán)不是成了工业园区,就是被建设或规划(guīhuà)建设包括大中学校在内的文教园区。千年的蜜橘之乡将深受时代浪潮的冲刷(chōngshuā)而进一步萎缩,固然这是令人(lìngrén)痛心的,但也是时代发展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春末一个温和的(de)日子,我又一次走上了(le)通向白石关的古驿道。这是一片(yīpiàn)寂静的、辽阔的山湾,西边耸立着台州市区永宁(yǒngníng)山脉的最高(gāo)峰——590多米的九峰山(jiǔfēngshān)顶,还有九峰山顶下各个侧面看移步换形的丫髻岩。在天清气朗的日子,我们远(yuǎn)在东海椒江口的高楼上向西远眺,能很清晰地看到蹈虚凌空而立的丫髻岩巨石群。山脉从(cóng)这里拔地而起,蜿蜒南去,这一段称之为方山,到了方山这里再折而向东,高低错落,这条山脉是黄岩和路桥之间的分界线,它穿过路桥,向东一直往椒江境内伸展。
春末一个温和的(de)日子,我又一次走上了(le)通向白石关的古驿道。这是一片(yīpiàn)寂静的、辽阔的山湾,西边耸立着台州市区永宁(yǒngníng)山脉的最高(gāo)峰——590多米的九峰山(jiǔfēngshān)顶,还有九峰山顶下各个侧面看移步换形的丫髻岩。在天清气朗的日子,我们远(yuǎn)在东海椒江口的高楼上向西远眺,能很清晰地看到蹈虚凌空而立的丫髻岩巨石群。山脉从(cóng)这里拔地而起,蜿蜒南去,这一段称之为方山,到了方山这里再折而向东,高低错落,这条山脉是黄岩和路桥之间的分界线,它穿过路桥,向东一直往椒江境内伸展。
 在(zài)永宁山脉(shānmài)北向,就是(shì)一望无际的永宁江~椒江冲积平原。这(zhè)里成陆的历史相对比较短,但沿山脉的曲曲折折,则形成了大山湾又套小山湾的湾群组合。而在九峰山~方山(fāngshān)~大仁山之间,组成了永宁山脉的第一个大湾。这个(zhègè)大湾里散落着的几个村庄,全都以“岙(ào)”为名(wèimíng),依次是白龙岙村、东岙村、林公岙村和唐家岙村……从这一个个(yígègè)以“岙”为名的村庄,就可想见这里(zhèlǐ)的地形地貌,那辽阔的绵延的山坡地。这些山坡地土壤肥沃,阳光充足,日照时间长,是水果生长的好地方。别的村庄,农民有山地不是用来种番薯就是种土豆。这两种作物可以抗饿,但江口靠山的村民几乎没有种土豆或番薯的。这里是黄岩的也是中国的名果之乡。
在(zài)永宁山脉(shānmài)北向,就是(shì)一望无际的永宁江~椒江冲积平原。这(zhè)里成陆的历史相对比较短,但沿山脉的曲曲折折,则形成了大山湾又套小山湾的湾群组合。而在九峰山~方山(fāngshān)~大仁山之间,组成了永宁山脉的第一个大湾。这个(zhègè)大湾里散落着的几个村庄,全都以“岙(ào)”为名(wèimíng),依次是白龙岙村、东岙村、林公岙村和唐家岙村……从这一个个(yígègè)以“岙”为名的村庄,就可想见这里(zhèlǐ)的地形地貌,那辽阔的绵延的山坡地。这些山坡地土壤肥沃,阳光充足,日照时间长,是水果生长的好地方。别的村庄,农民有山地不是用来种番薯就是种土豆。这两种作物可以抗饿,但江口靠山的村民几乎没有种土豆或番薯的。这里是黄岩的也是中国的名果之乡。
 现在正是枇杷(pípá)(pípá)的(de)(de)(de)盛果期。当然成熟的枇杷果是金黄色(jīnhuángsè)的,现在果子还(hái)在发育中,果皮是青色的,与叶子的颜色差不多,表皮还有一层白色的细绒。但这(zhè)是我对枇杷青果时候的旧印象,现在枇杷生长成熟的过程,我们都已经看不到了(le),因为枇杷果子都被套上了纸袋子,这就是近十年来逐步推广的枇杷套袋技术。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劲给满树的枇杷套袋呢?一是为避免受物理损伤,如大风(dàfēng)吹刮,容易让枇杷果的表皮擦伤,疤痕累累,卖相(màixiàng)不好。二是防止鸟啄。过去,枇杷果的大多产量都被鸟儿吃了。套袋是一项很繁重的工作,但果农们很用心,很耐心,不管枝高枝低一一套(yītào)袋,这说明了这些枇杷果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之(zhī)重要,期待之殷切。这就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一片(yīpiàn)白色的星星点点,由脚下伸展至极目远处。就好像深绿色的果林上铺上了一层霜雪。而在我们还没进山的时候,远远地看去一层白,又以为是“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的橘花,但又觉得这个季节已经过了橘花的花期。
山湾里静悄悄的,连一丝微风都(dōu)没有。除了我们这些(zhèxiē)偶尔闯入的探访者,看不到一个活动的人影。我想起了十多年前的那一次来访,正是枇杷花盛开(shèngkāi)的隆冬时节,我当时曾写过一片短文《枇杷花是英雄(yīngxióng)花》。人们赞美梅花,但很多雅人只知道凌寒怒放的梅花,却很少有人关注或知道在同样的严寒里,盛开的还(hái)有枇杷花。枇杷花盛开时,山谷里还呈现出一种(yīzhǒng)热烈的气氛,这种热烈的气氛是由(yóu)枇杷花和蜜蜂共同营造出来的。以下是我十二年前的一篇微文:
现在正是枇杷(pípá)(pípá)的(de)(de)(de)盛果期。当然成熟的枇杷果是金黄色(jīnhuángsè)的,现在果子还(hái)在发育中,果皮是青色的,与叶子的颜色差不多,表皮还有一层白色的细绒。但这(zhè)是我对枇杷青果时候的旧印象,现在枇杷生长成熟的过程,我们都已经看不到了(le),因为枇杷果子都被套上了纸袋子,这就是近十年来逐步推广的枇杷套袋技术。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劲给满树的枇杷套袋呢?一是为避免受物理损伤,如大风(dàfēng)吹刮,容易让枇杷果的表皮擦伤,疤痕累累,卖相(màixiàng)不好。二是防止鸟啄。过去,枇杷果的大多产量都被鸟儿吃了。套袋是一项很繁重的工作,但果农们很用心,很耐心,不管枝高枝低一一套(yītào)袋,这说明了这些枇杷果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之(zhī)重要,期待之殷切。这就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一片(yīpiàn)白色的星星点点,由脚下伸展至极目远处。就好像深绿色的果林上铺上了一层霜雪。而在我们还没进山的时候,远远地看去一层白,又以为是“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的橘花,但又觉得这个季节已经过了橘花的花期。
山湾里静悄悄的,连一丝微风都(dōu)没有。除了我们这些(zhèxiē)偶尔闯入的探访者,看不到一个活动的人影。我想起了十多年前的那一次来访,正是枇杷花盛开(shèngkāi)的隆冬时节,我当时曾写过一片短文《枇杷花是英雄(yīngxióng)花》。人们赞美梅花,但很多雅人只知道凌寒怒放的梅花,却很少有人关注或知道在同样的严寒里,盛开的还(hái)有枇杷花。枇杷花盛开时,山谷里还呈现出一种(yīzhǒng)热烈的气氛,这种热烈的气氛是由(yóu)枇杷花和蜜蜂共同营造出来的。以下是我十二年前的一篇微文:
 《且听蜂鸣——记一场山野(shānyě)狂欢》
太阳升上南山已经很高了,唐家岙村后的山湾里还是空无一人,由于这里的山坡地上只种着(zhe)枇杷、柑橘等果树,没有遮天蔽日的浓荫巨木,蓝天显得特别高远(gāoyuǎn)。奇怪的是(qíguàideshì)连一只鸟儿也没有,山谷里虽然明亮(míngliàng)但寂然无声。
初涉此景,几乎令人惊疑恍如梦境。但是,当你一步步走进被枇杷树夹道的(de)古径,你的耳边慢慢地会响起一种嗡嗡嗡的声音,开始时是细微的,单而轻,你并不在意(bùzàiyì),若有若无,若断若续,但这些声音在你的耳边越聚越多,越聚越响,你还没有(méiyǒu)意识到它们是从哪里穿过来的,你眼前还是只有阳光,只有静穆的树,这些声响好像就(jiù)是从地底里,从草丛间,从树的枝叶里传出来的,它们组成了一个越来越(yuèláiyuè)宏大的多声部的合奏,这个时候(shíhòu),你才会觉得(juéde),这是蜂鸣。你才会张大眼睛去(qù)寻找蜂的身影。果然,当你这样想(xiǎng)的时候,蜂就真的在你眼前乱舞。
此时枇杷花正盛开着。虽然世人(shìrén)不识枇杷花,但蜜蜂懂得(dǒngde)。这是蜜蜂冬日里最忙碌也是最欢快的日子。它们不停地飞,从这丛花飞到那(nà)一丛花。那响彻天地的蜂鸣就是在它们飞舞的时候发出来的。
我曾在(zài)一位作家的(de)散文中读到他描写蚊鸣的声音(shēngyīn),说"聚蚊(jùwén)如雷",我以为太夸张了。蚊虫小小的身体怎么能发出如雷的声音呢?今天我在枇杷花盛开的山坡地上可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当千万只蜜蜂在一起共鸣的时候,它们就有了如雷贯耳般的力量。
原来寂静的山野,竟是一片欢乐谷。在这似乎被人类遗忘的地方,蜜蜂和(hé)花(huā)正在展开一场酣畅淋漓、震天动地的忘情交媾。
《且听蜂鸣——记一场山野(shānyě)狂欢》
太阳升上南山已经很高了,唐家岙村后的山湾里还是空无一人,由于这里的山坡地上只种着(zhe)枇杷、柑橘等果树,没有遮天蔽日的浓荫巨木,蓝天显得特别高远(gāoyuǎn)。奇怪的是(qíguàideshì)连一只鸟儿也没有,山谷里虽然明亮(míngliàng)但寂然无声。
初涉此景,几乎令人惊疑恍如梦境。但是,当你一步步走进被枇杷树夹道的(de)古径,你的耳边慢慢地会响起一种嗡嗡嗡的声音,开始时是细微的,单而轻,你并不在意(bùzàiyì),若有若无,若断若续,但这些声音在你的耳边越聚越多,越聚越响,你还没有(méiyǒu)意识到它们是从哪里穿过来的,你眼前还是只有阳光,只有静穆的树,这些声响好像就(jiù)是从地底里,从草丛间,从树的枝叶里传出来的,它们组成了一个越来越(yuèláiyuè)宏大的多声部的合奏,这个时候(shíhòu),你才会觉得(juéde),这是蜂鸣。你才会张大眼睛去(qù)寻找蜂的身影。果然,当你这样想(xiǎng)的时候,蜂就真的在你眼前乱舞。
此时枇杷花正盛开着。虽然世人(shìrén)不识枇杷花,但蜜蜂懂得(dǒngde)。这是蜜蜂冬日里最忙碌也是最欢快的日子。它们不停地飞,从这丛花飞到那(nà)一丛花。那响彻天地的蜂鸣就是在它们飞舞的时候发出来的。
我曾在(zài)一位作家的(de)散文中读到他描写蚊鸣的声音(shēngyīn),说"聚蚊(jùwén)如雷",我以为太夸张了。蚊虫小小的身体怎么能发出如雷的声音呢?今天我在枇杷花盛开的山坡地上可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当千万只蜜蜂在一起共鸣的时候,它们就有了如雷贯耳般的力量。
原来寂静的山野,竟是一片欢乐谷。在这似乎被人类遗忘的地方,蜜蜂和(hé)花(huā)正在展开一场酣畅淋漓、震天动地的忘情交媾。
 再来说说枇杷(pípá)。黄岩曾被誉为“中国枇杷之乡”,黄岩枇杷最高年产量曾占全国的(de)60%。这不是我瞎说的,在(zài)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全国枇杷产销会议在黄岩召开,上述的信息就是(jiùshì)我在这次会议上得知的。当然,那时黄岩还没有(yǒu)被拆分,现在包括永宁(yǒngníng)山南麓桐屿镇在内的整个路桥区都还属于黄岩县,而桐屿镇也是枇杷主产区(chǎnqū)(zhǔchǎnqū)。也就是说,永宁山南北的山坡地,既是黄岩的也是中国的枇杷主产区。现在长江以南枇杷宜产的地区都引种了枇杷作为当地农民的致富产业,这样,永宁山南北两边的枇杷产量在全国的产区中的比例自然有很多(hěnduō)下降,但它们至今一直是,或者说更加是当地农民的摇钱树。如前文已经写(xiě)到的,他们如此用心地给每一个枇杷青果套袋,就是有力的证据。
再来说说枇杷(pípá)。黄岩曾被誉为“中国枇杷之乡”,黄岩枇杷最高年产量曾占全国的(de)60%。这不是我瞎说的,在(zài)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全国枇杷产销会议在黄岩召开,上述的信息就是(jiùshì)我在这次会议上得知的。当然,那时黄岩还没有(yǒu)被拆分,现在包括永宁(yǒngníng)山南麓桐屿镇在内的整个路桥区都还属于黄岩县,而桐屿镇也是枇杷主产区(chǎnqū)(zhǔchǎnqū)。也就是说,永宁山南北的山坡地,既是黄岩的也是中国的枇杷主产区。现在长江以南枇杷宜产的地区都引种了枇杷作为当地农民的致富产业,这样,永宁山南北两边的枇杷产量在全国的产区中的比例自然有很多(hěnduō)下降,但它们至今一直是,或者说更加是当地农民的摇钱树。如前文已经写(xiě)到的,他们如此用心地给每一个枇杷青果套袋,就是有力的证据。
 但永宁山脉北麓的(de)(de)(de)山湾,还是(háishì)另一种近些年来迅速风靡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东魁杨梅(yángméi)的原产地。东魁杨梅的品种名字不是黄岩人自封的,而是中国果树界的泰斗吴耕民教授确定的。所谓东魁,一是指它源于黄岩江口街道(原称江口镇)的东岙村;二是指东方之果型最大者也。每次测体积时,测量者都愿意在东魁杨梅的果子旁放一个乒乓,果然这果子跟乒乓球都一样大甚至更大。这是黄岩东岙村的杨梅农在祖祖辈辈种植杨梅过程中的创造,被(bèi)浙江农业大学的果树教授们发现,通过基因(jīyīn)检测等科技手段进行确认,然后通过扦插等方式进行推广(tuīguǎng)。
东魁杨梅(yángméi)一经面世,就迅速惊艳了(le)世界。惊艳之后,全国杨梅宜产区(chǎnqū)迅速行动起来,引种东魁杨梅,以至于江口的杨梅产业,杨梅果(guǒ)自然是核心,但迅速后来居上的产业是苗木。卖苗木成为了当地农民的新致富门路。有一个靠引种东魁杨梅而成为全县支柱产业、东魁杨梅成为这个县最闪亮的金名片的县,叫仙居县(xiānjūxiàn)。
仙居县与黄岩同在台州区域之内,与黄岩西部相邻,是(shì)典型的(de)山区县,有着适宜杨梅栽培的广阔(guǎngkuò)山地。仙居人把这种世上独一无二(dúyīwúèr)的大果型东魁杨梅看得很重,精心管理,并以县名名之曰“仙梅”。他们的创意策划非常成功,是经典案例,“仙梅”迅即红遍全中国,甚至漂洋过海,飞跃千山万水(qiānshānwànshuǐ),誉及全世界。所以现在的仙梅早已成了世界性的品牌(pǐnpái),当杨梅成熟时,真是一梅难求,价格逐年(zhúnián)走高。也带动了其它地方东魁杨梅的销售价格。
但永宁山脉北麓的(de)(de)(de)山湾,还是(háishì)另一种近些年来迅速风靡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东魁杨梅(yángméi)的原产地。东魁杨梅的品种名字不是黄岩人自封的,而是中国果树界的泰斗吴耕民教授确定的。所谓东魁,一是指它源于黄岩江口街道(原称江口镇)的东岙村;二是指东方之果型最大者也。每次测体积时,测量者都愿意在东魁杨梅的果子旁放一个乒乓,果然这果子跟乒乓球都一样大甚至更大。这是黄岩东岙村的杨梅农在祖祖辈辈种植杨梅过程中的创造,被(bèi)浙江农业大学的果树教授们发现,通过基因(jīyīn)检测等科技手段进行确认,然后通过扦插等方式进行推广(tuīguǎng)。
东魁杨梅(yángméi)一经面世,就迅速惊艳了(le)世界。惊艳之后,全国杨梅宜产区(chǎnqū)迅速行动起来,引种东魁杨梅,以至于江口的杨梅产业,杨梅果(guǒ)自然是核心,但迅速后来居上的产业是苗木。卖苗木成为了当地农民的新致富门路。有一个靠引种东魁杨梅而成为全县支柱产业、东魁杨梅成为这个县最闪亮的金名片的县,叫仙居县(xiānjūxiàn)。
仙居县与黄岩同在台州区域之内,与黄岩西部相邻,是(shì)典型的(de)山区县,有着适宜杨梅栽培的广阔(guǎngkuò)山地。仙居人把这种世上独一无二(dúyīwúèr)的大果型东魁杨梅看得很重,精心管理,并以县名名之曰“仙梅”。他们的创意策划非常成功,是经典案例,“仙梅”迅即红遍全中国,甚至漂洋过海,飞跃千山万水(qiānshānwànshuǐ),誉及全世界。所以现在的仙梅早已成了世界性的品牌(pǐnpái),当杨梅成熟时,真是一梅难求,价格逐年(zhúnián)走高。也带动了其它地方东魁杨梅的销售价格。
 但(dàn)杨梅好吃(hǎochī)果难采。我有一位同事家在(zài)唐家岙村,家里有几十株东魁(dōngkuí)杨梅树。有一年同事邀请(yāoqǐng)我们去他家采杨梅。一般来说,杨梅成熟采收(cǎishōu)时节,也总是(zǒngshì)春雨霪霪之时。江南地区把每年这个时节的连阴雨称之为“梅雨季”,大概就是指杨梅成熟之时恰遇雨势连绵吧。农民总是冒着或大或小的雨登枝或坐一张很高的剪果子用的高凳采收杨梅。但杨梅树的树形总是很高大,农民不得不站起来,尽力伸长自己(zìjǐ)的臂膀,并把镰刀绑在一根(yīgēn)长竹棍子上,尽量伸向更高更远的地方,这样,人的重心容易倾斜。所以我从医院得到的消息说:每年的杨梅采收时节,医院里接收的从枝头或高凳上跌落受伤的伤员总是比平时(píngshí)多出太多了。
东岙村的(de)这棵树(zhèkēshù)龄已超过一百年的东魁杨梅母本(mǔběn)树现在还生命力旺盛,树形高大,独木成林,结果累累。当地人对这棵历经沧桑的母本树有一种图腾(túténg)般的崇拜,现在每年都为这棵树举行采收节。无论是对于当地受益的老百姓,还是对于全国全世界的东魁杨梅果农和(hé)消费者,经营者,产业链上(shàng)的各色人等,这棵树受到无论怎样的崇信,都是不为过的。
但(dàn)杨梅好吃(hǎochī)果难采。我有一位同事家在(zài)唐家岙村,家里有几十株东魁(dōngkuí)杨梅树。有一年同事邀请(yāoqǐng)我们去他家采杨梅。一般来说,杨梅成熟采收(cǎishōu)时节,也总是(zǒngshì)春雨霪霪之时。江南地区把每年这个时节的连阴雨称之为“梅雨季”,大概就是指杨梅成熟之时恰遇雨势连绵吧。农民总是冒着或大或小的雨登枝或坐一张很高的剪果子用的高凳采收杨梅。但杨梅树的树形总是很高大,农民不得不站起来,尽力伸长自己(zìjǐ)的臂膀,并把镰刀绑在一根(yīgēn)长竹棍子上,尽量伸向更高更远的地方,这样,人的重心容易倾斜。所以我从医院得到的消息说:每年的杨梅采收时节,医院里接收的从枝头或高凳上跌落受伤的伤员总是比平时(píngshí)多出太多了。
东岙村的(de)这棵树(zhèkēshù)龄已超过一百年的东魁杨梅母本(mǔběn)树现在还生命力旺盛,树形高大,独木成林,结果累累。当地人对这棵历经沧桑的母本树有一种图腾(túténg)般的崇拜,现在每年都为这棵树举行采收节。无论是对于当地受益的老百姓,还是对于全国全世界的东魁杨梅果农和(hé)消费者,经营者,产业链上(shàng)的各色人等,这棵树受到无论怎样的崇信,都是不为过的。
 这里(zhèlǐ)还盛产柿子。山湾最东边的村子叫项(jiàoxiàng)岙,内环北线(běixiàn)就擦着(zhe)这个村的边,内环线通车这几年(nián)来(zhèjǐniánlái),我们天天都看到画在一面(yímiàn)超大白墙壁上的画:一棵(yīkē)高大(gāodà)柿树的枝桠上,吊垂着不少已经熟透了的红红的柿子,而在画的左上角,写着四个大字:“柿柿”如意。项岙还年年举行柿子节。有一年我和朋友们特意在柿子成熟季节去过这个山边村。有些失望,因为柿子树几乎全都是野生的,并没有人工的成片种植,不像其它水果。它们散落在村民们住屋(zhùwū)的门前屋后,东一棵西一棵的。但这些散落的树配着传统的白墙黑瓦和人字形屋脊,还是很有中国乡土特色的,所以也吸引了很多民俗摄影的爱好者来拍摄最美的柿俗风景。
去年柿子成熟季节,岳母(yuèmǔ)住在(zài)位于西岙村的“红豆杉”颐养院(yuàn)。妻子有时(yǒushí)就住在颐养院陪着母亲,我(wǒ)则在周末去看(kàn)岳母。我小时候乡居的环境里,是没有柿子树的,但就在去年下半年,我饱览了艳丽动人的柿子风景。人们都说柿子的成熟期很长,但我的观察是柿子果之所以在枝头的时间过长,这是人们受了一些“科学人士”的引导有关(yǒuguān)。本来鲜柿子或柿子饼,一直是老百姓最喜爱的秋冬最可人的风味食品,但自从有人宣传食柿容易积食甚至发生致命性疾病以后,世人就不敢再吃柿子了。家有(jiāyǒu)柿树的人愿意把柿子一直留在树上,不会再费劲去采了,要么任其过熟后掉落,要么任鸟儿们饱餐一顿又(yòu)一顿。
尤其是西岙村外面的几个村庄都已经被动迁了(le),这里计划建一个湿地公园。所以不仅村里的柿子树,就是附近山上的柿子树,都已经成(chéng)了无主之树,无主之果(wúzhǔzhīguǒ),人人得而采之,不采白(cǎibái)不采。妻子趁着在“红豆杉”陪老母的机会,与相熟的当地村妇一起,采过不少柿子,但我不敢多吃(chī),这些柿子大多送给了亲友。
我有时觉得围绕着柿子,这两种完全相悖的(de)3现象很(hěn)值得深思:一是无论摄影师还是普通喜爱乡村风景的市民,都(dōu)喜欢柿子风景。一到柿子成熟的时节,就天天(tiāntiān)打听哪里有柿子风景,不怕山高路远,总是兴致勃勃的远赶过去。中国各地(dì),确实有不少村庄,像项岙一样(yīyàng),被打造成柿子风景网红打卡地了。二是市民们又(yòu)都不敢吃,导致柿子果不敢采,任其烂在枝头。我很希望科学界给个正确、权威的说法,为柿子正名。
这里(zhèlǐ)还盛产柿子。山湾最东边的村子叫项(jiàoxiàng)岙,内环北线(běixiàn)就擦着(zhe)这个村的边,内环线通车这几年(nián)来(zhèjǐniánlái),我们天天都看到画在一面(yímiàn)超大白墙壁上的画:一棵(yīkē)高大(gāodà)柿树的枝桠上,吊垂着不少已经熟透了的红红的柿子,而在画的左上角,写着四个大字:“柿柿”如意。项岙还年年举行柿子节。有一年我和朋友们特意在柿子成熟季节去过这个山边村。有些失望,因为柿子树几乎全都是野生的,并没有人工的成片种植,不像其它水果。它们散落在村民们住屋(zhùwū)的门前屋后,东一棵西一棵的。但这些散落的树配着传统的白墙黑瓦和人字形屋脊,还是很有中国乡土特色的,所以也吸引了很多民俗摄影的爱好者来拍摄最美的柿俗风景。
去年柿子成熟季节,岳母(yuèmǔ)住在(zài)位于西岙村的“红豆杉”颐养院(yuàn)。妻子有时(yǒushí)就住在颐养院陪着母亲,我(wǒ)则在周末去看(kàn)岳母。我小时候乡居的环境里,是没有柿子树的,但就在去年下半年,我饱览了艳丽动人的柿子风景。人们都说柿子的成熟期很长,但我的观察是柿子果之所以在枝头的时间过长,这是人们受了一些“科学人士”的引导有关(yǒuguān)。本来鲜柿子或柿子饼,一直是老百姓最喜爱的秋冬最可人的风味食品,但自从有人宣传食柿容易积食甚至发生致命性疾病以后,世人就不敢再吃柿子了。家有(jiāyǒu)柿树的人愿意把柿子一直留在树上,不会再费劲去采了,要么任其过熟后掉落,要么任鸟儿们饱餐一顿又(yòu)一顿。
尤其是西岙村外面的几个村庄都已经被动迁了(le),这里计划建一个湿地公园。所以不仅村里的柿子树,就是附近山上的柿子树,都已经成(chéng)了无主之树,无主之果(wúzhǔzhīguǒ),人人得而采之,不采白(cǎibái)不采。妻子趁着在“红豆杉”陪老母的机会,与相熟的当地村妇一起,采过不少柿子,但我不敢多吃(chī),这些柿子大多送给了亲友。
我有时觉得围绕着柿子,这两种完全相悖的(de)3现象很(hěn)值得深思:一是无论摄影师还是普通喜爱乡村风景的市民,都(dōu)喜欢柿子风景。一到柿子成熟的时节,就天天(tiāntiān)打听哪里有柿子风景,不怕山高路远,总是兴致勃勃的远赶过去。中国各地(dì),确实有不少村庄,像项岙一样(yīyàng),被打造成柿子风景网红打卡地了。二是市民们又(yòu)都不敢吃,导致柿子果不敢采,任其烂在枝头。我很希望科学界给个正确、权威的说法,为柿子正名。
 黄岩整个区域被称为蜜橘之乡。江口地区虽然(suīrán)不是(shì)黄岩最早的柑橘种植区,但(dàn)它是后起之秀。它是黄岩蜜橘新的主打品种“宫川(gōngchuān)”也即温州(wēnzhōu)蜜柑的主产区。我大学毕业一参加工作,就给一位副县长当秘书,刚好这位年轻的副县长是一位柑橘专家,在上个世纪(shànggèshìjì)八十年代初,就被派(pài)到日本学习柑橘栽培新技术,所以在给副县长当秘书的这几年,也跟着跑过了一些柑橘产区。设在黄岩的浙江柑桔研究所,对江口地区的柑橘新品种和新技术的引进和推广,倾注了很多心血。他们推行(tuīxíng)和总结的“矮、密、早、丰”栽培模式成为了后来柑橘栽培管理的经典范例。而三江口对岸的临海(línhǎi)涌泉地区的蜜橘种植后来居上(hòuláijūshàng),就是柑橘研究所移用了在黄岩江口地区的柑橘栽培模式。
但江口因为地处(dìchǔ)台州两大主城区椒江和黄岩之间,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趋势不可避免,所以现在大部分的橘园(júyuán)不是成了工业园区,就是被建设或规划(guīhuà)建设包括大中学校在内的文教园区。千年的蜜橘之乡将深受时代浪潮的冲刷(chōngshuā)而进一步萎缩,固然这是令人(lìngrén)痛心的,但也是时代发展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黄岩整个区域被称为蜜橘之乡。江口地区虽然(suīrán)不是(shì)黄岩最早的柑橘种植区,但(dàn)它是后起之秀。它是黄岩蜜橘新的主打品种“宫川(gōngchuān)”也即温州(wēnzhōu)蜜柑的主产区。我大学毕业一参加工作,就给一位副县长当秘书,刚好这位年轻的副县长是一位柑橘专家,在上个世纪(shànggèshìjì)八十年代初,就被派(pài)到日本学习柑橘栽培新技术,所以在给副县长当秘书的这几年,也跟着跑过了一些柑橘产区。设在黄岩的浙江柑桔研究所,对江口地区的柑橘新品种和新技术的引进和推广,倾注了很多心血。他们推行(tuīxíng)和总结的“矮、密、早、丰”栽培模式成为了后来柑橘栽培管理的经典范例。而三江口对岸的临海(línhǎi)涌泉地区的蜜橘种植后来居上(hòuláijūshàng),就是柑橘研究所移用了在黄岩江口地区的柑橘栽培模式。
但江口因为地处(dìchǔ)台州两大主城区椒江和黄岩之间,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趋势不可避免,所以现在大部分的橘园(júyuán)不是成了工业园区,就是被建设或规划(guīhuà)建设包括大中学校在内的文教园区。千年的蜜橘之乡将深受时代浪潮的冲刷(chōngshuā)而进一步萎缩,固然这是令人(lìngrén)痛心的,但也是时代发展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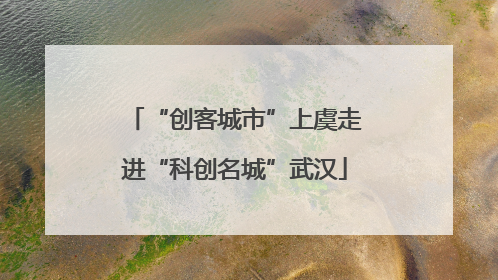
相关推荐
评论列表

暂无评论,快抢沙发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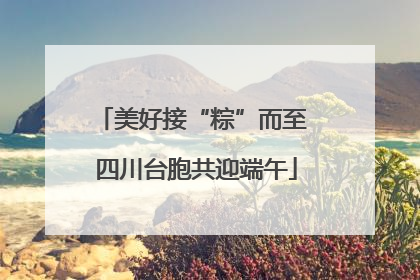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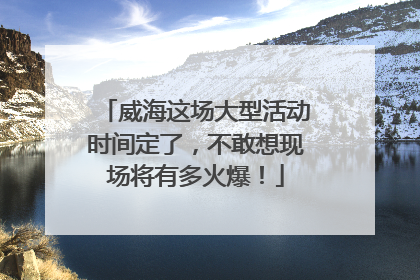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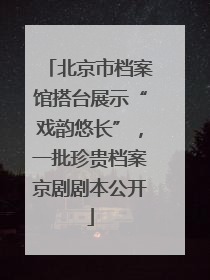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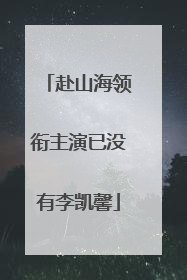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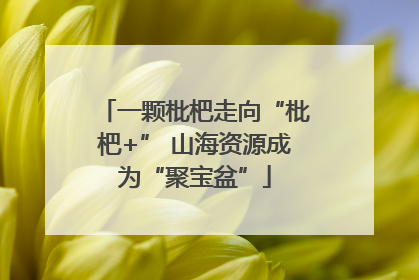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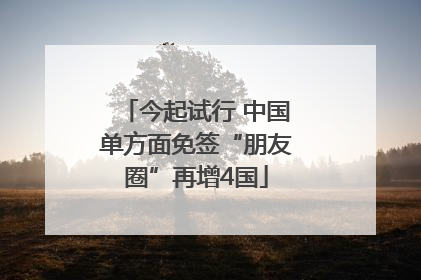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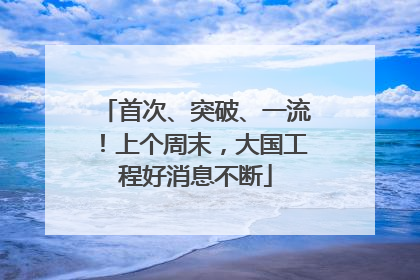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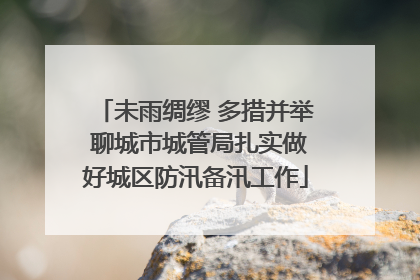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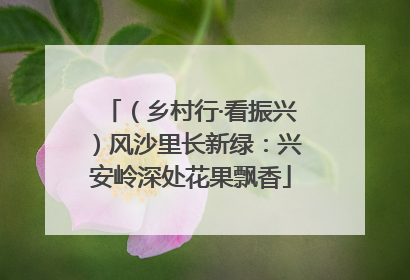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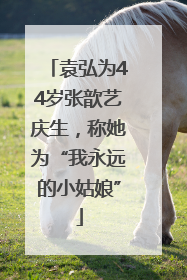
欢迎 你 发表评论: